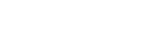我出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镇吐格曼艾日克村,一个地处天山南麓、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小村落,吐格曼艾日克译为“水渠边的石磨”,也正如其意,我们村周边牧草茂密、河水绕村而过,曾是古龟兹国的繁锦之地。
然而,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家乡由于地理位置偏远、基础设施落后,“看病难”的问题非常突出,依稀记得村里的人生病都是靠着“土方子”缓解。我对那时“父亲半夜爬起,套上驴车进城寻医”的画面印象极其深刻。爷爷奶奶长期患病,父亲每次都是套上驴车,带他们各大医院到处跑。由于医疗条件、诊疗技术落后,治疗效果并不理想,无奈的父亲常常赶着驴车抹着眼泪。2010年,母亲突然离世,一向开朗的父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。“学医”的念想从那会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高考结束,我如愿考取了新疆医科大学。2012年,我又考取日本香川大学医学部。
出国前一夜,父亲与我促膝长谈,聊了许久。“我们生在农村、根在中国,将来不管有多大的本事,不能忘了家乡人,更不能忘了自己的国家。”父亲的这番话,成了我求学立业的座右铭。
初到日本,我感觉非常不习惯。一方面要进一步学习日语、英语,“语言关”在短时间难以克服;另一方面还要接触更加复杂的专业术语,理解起来比较吃力。面对诸多困难,我并没有因此而退却。
为更快攻破语言关,我把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当成学习语言的实践平台,成功突破了交流障碍;为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,我经常自主加压“开小灶”,从死记硬背、一知半解再到完全理解,掌握了很多新知识。留学期间,我又申请了助学金、获得了奖学金;县乡联合协调解决了我妻子的就业和女儿的入学问题……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,让我免除了对学费、生活费及家庭的后顾之忧;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,让我身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。
凝聚着思乡情和报国梦,我在8年的时间里,争分夺秒、刻苦学习,先后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了8篇论文,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业。毕业之际,导师盛情邀请我留在日本,我摇头婉拒:“留下来固然能有更丰厚的报酬待遇和更优越的科研环境,但我的家乡需要我把更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去。”
回国后,到一线还是去城里,我又陷入两难。那会儿,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正在组建,正是用人之际,但留在城市更能好发挥专业优势和自己的专长。
如何选择?犹豫之际,我带着疑问回到了母校。
“你刚回国,医疗经验还不够丰富,大医院的平台相对更广,能接触更多的专家和病人,积累更多经验,也能更好地发挥你的特长优势,把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应用在更宽阔的领域。”母校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我。最终我选择入职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。
入职后,医院党组织和新和县委、县政府在工作生活上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。为帮助我尽快适应国内环境,医院党委专门制订了“一对一”帮带方案,院领导、科室主任与我结成捆绑对子,鼓励我发挥专业优势,牵头组建医疗技术攻关团队。新和县委、县政府又将我纳入“医疗人才储备库”中,县领导经常与我联系,询问生活中的困难,并协助办理我女儿转学和家属体检等事宜……这些来自党和政府及单位的关心关爱,让我倍感温暖,进一步坚定了我要以自身所学服务家乡的决心。
工作以来,我始终牵挂着家乡。每年回老家探亲,村里或附近乡镇的患者都会来找我帮忙看诊,不管什么时候,我都是来者不拒、热情服务。有的拿着县医院的诊断结果找我帮忙看看,有的直接把影像检查结果资料通过微信发给我,我尽可能帮他们分析病情,有些把握不准的就会请医院的专家帮忙一起看,为他们提供一些医疗建议。
前年,老家村里有位病人患有腰椎结核病,疼痛剧烈,脊柱屈伸、侧弯和旋转活动都受到限制,他甚至都已经写好了遗书。我了解到情况后,主动接他到友谊医院就诊,并帮他办理了住院、协调了手术、垫付了医药费。痊愈后,他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。
新和县玉奇喀特镇患者海力且木·艾买尔曾在一场意外中导致股骨颈骨折,后因治疗不及时引发“股骨头缺血坏死”,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,生活难自理,出门更是一种奢望。去年,联系到我后,我多次上门问询病因、查看病情,经过集中诊治,让她彻底扔掉了拄了22年的拐杖。
如今,在我的通讯录里还有51个这样的特殊联系人,有渭干乡的老张,兰帕村的吐拉甫,苏帕墩村的赛买提……
工作这些年,我从“海归博士”转变成了“健康卫士”。我和许多看病的群众从医患关系变成了亲密朋友,我也从大家嘴里的“艾医生”“艾专家”变成了“小艾”“艾巴郎”。有些村民说:想不到我们不出国,也能在家门口见到“洋大夫”。这些浓浓的家乡情,让我无悔自己最初的选择。未来,我会继续学习深造,提升医疗技术,减轻更多父老乡亲的病痛。
(李高 刘灵慧 整理)